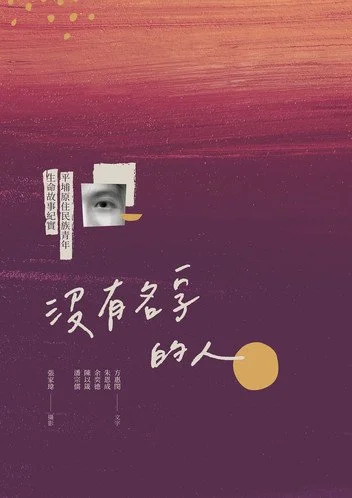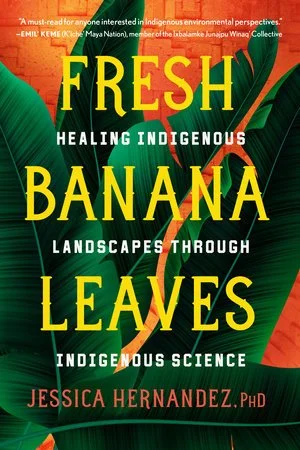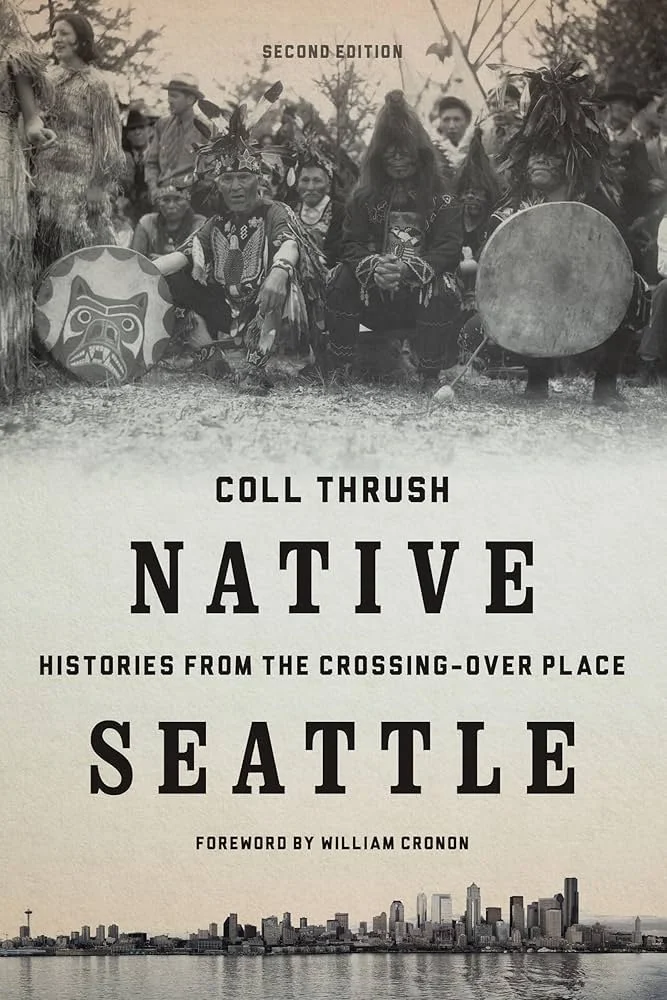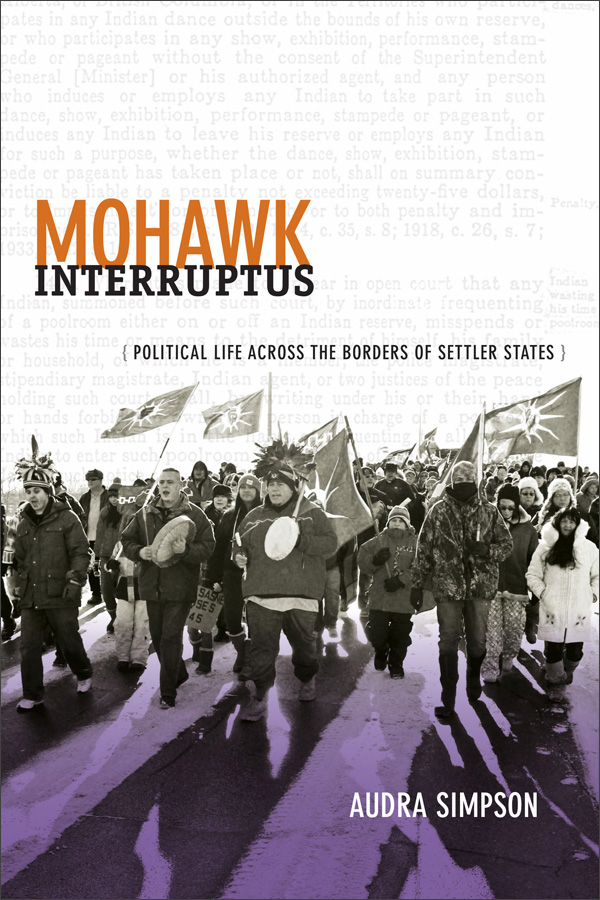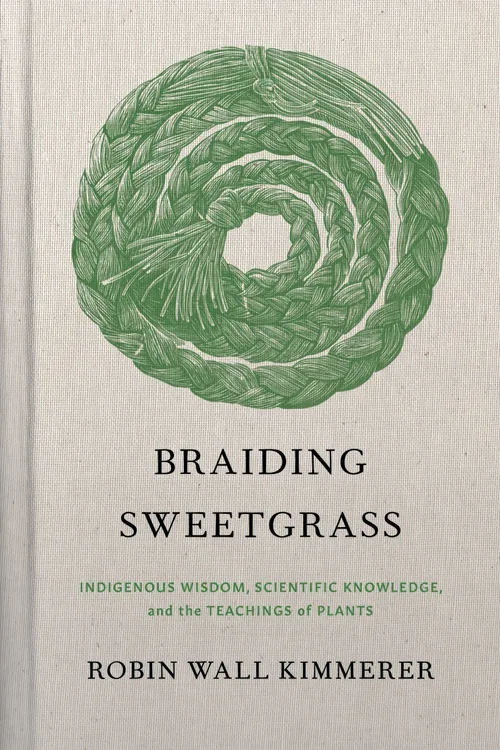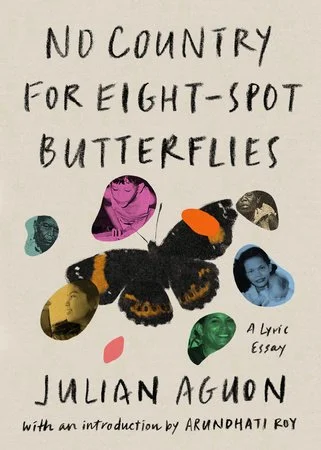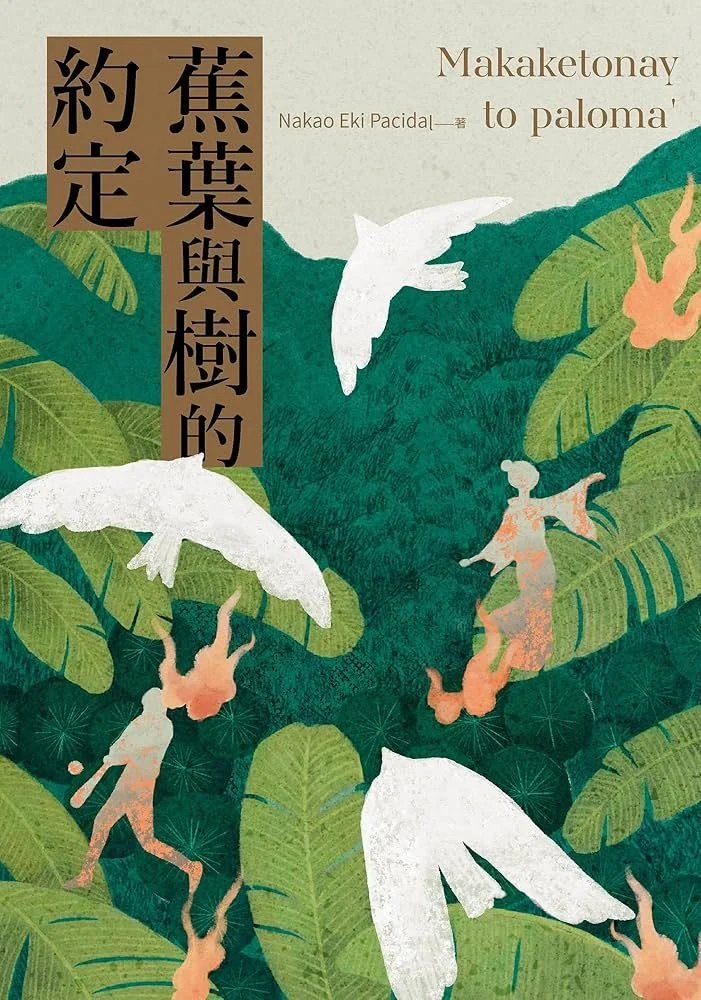資源中心
研究 & 出版品
-
-
Lin, H. (2025). Indigenou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actices in the Cou Saviki Tribal Classroom in Taiw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u, Margaret Yun-Pu (Nikal Kabala’an). 2025. “A System Not of Our Making: Electoral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 in Taiwan.” Taiwan Politics, July, 1–17.
-
Nikal, Yun-Pu Tu (2023). 當原民服裝成為校園演出的道具?你眼裡的「文化展示」,是對我傷口的踩踏|人文思想, 法律白話文運動.
Hou, Y. -H., Kabala’an, N., and Lin, H. (2024). Indigenous Language Education in Taiwan: From Language Preservation to Community-Based Learning.Taiwan Insight.
Margaret Yun-Pu Tu (2025). Taiwan’s Barrier Lake Disaster Intersects With Its Troubled Indigenous Policy: The Fata’an tribal community wants to remain in its ancestral home during the rebuilding process.
【投書】離災不離鄉:為什麼馬太鞍需要「中繼安置」?旅外阿美族人寫給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封信 by Nikal 杜芸璞、Ohay Angah
Yun-Pu Tu (2024),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aiwan Human Rights Hub.
精選故事
-
完美受害者迷思
近期花蓮光復鄉馬太鞍部落的救災及復原中,在社群媒體上也有許多網友分享在救災時接受到部落族人的感謝,受邀吃飯喝酒,也或分享被受邀八月祭典時來參與,相關貼文下也有許多留言表示,此邀請為族人表達感謝的方式,也同時提醒漢人網友要尊重部落的界線,要注意漢人對於情緒的規訓及慈善的概念容易變成殖民的重演。
我們從這個實例,也可見對完美受害的迷思在網路時代透過社群媒體更加迅速地發酵。無論是國軍拍照上傳到Instagram或Threads,或災民與志工苦中作樂的影像,都成為輿論批評與公審的對象。網路影像的片面解讀,壓縮了災難經驗的全面性與複雜性,使災難被框限為單一、純粹且扁平的苦痛展演。
當城市居民對鄉鎮居民有這種對完美受害處境的期待,尤其是對原住民族社群所在的鄉鎮時,這樣的期待則進一步鞏固了原漢關係中的漢人中心思維。
對原住民部落而言,災後的情緒表現與文化實踐,如歌唱、舞蹈、祭儀與日常的歡笑,常是集體療癒與社會重建的重要資源;若外界以表面的悲傷展演來評判,則可能錯失這些實踐對於部落自我修復的重要意義,阻礙了由部落主導、部落居民為核心的修復之路。
以自決權與賦能出發的助人
提到自我修復-- 在我們上一篇的文章中也呼籲中央與地方政府重視部落需要「中繼安置計畫」,在這裡,我們想延伸討論救災及助人時,有哪些觀點可以幫助我們避免在救災中加深結構性不平等,介入時如何以原住民族的世界觀為出發點,以原住民族的自決權為主?以賦能而非為其做決定?
馬太鞍居民在受災的經驗之前,是擁有完整生活與喜怒哀樂的人; 部落在9/23之前,是擁有千年的傳統智慧、年齡階層組織、生活方式、經濟體系的社會。然而,不管是在媒體描述上,還是大眾對於災難的想像,受災的個人及群體往往被外者貼上「受災者/ 受助者/ 受害者」這樣扁平的標籤,被剝奪去詮釋自己與此災難的關係的機會。
在當代社會的災難敘事與媒體詮釋中,「完美受害者」的想像往往潛藏於情感的公共展示。受災者被期待以可辨識且符號化的苦難姿態現身,以悲痛、沉默、無助的樣貌回應社會對「真實受苦」的投射。尤其再加上台灣漢人社會長期對原住民族的刻板意象及隱微歧視(microaggression) 之下(比方說「原住民很樂觀」等的說詞)[註一],唯有當苦難被以具體的形象呈現,公眾的同情、媒體的報導與制度性的救援行動方得以獲得正當性。由此,「救助者」與「被救助者」的關係彷彿構成一種倫理劇場,生產出道德的資本。相對地,那些未依循此情感劇本的災民,則被視為「不夠悲痛」或「不夠純粹」。當災民展現出堅毅、幽默或自娛的姿態,其獲得關注與援助的正當性反而遭到大眾質疑。
以關係為本的救災,避免文化殖民
九二一及莫拉克颱風正呈現了政府對「被救助者」的需求的想像,這兩個災難後,政府採取建構永久屋的方式安置災民,但這樣的計畫不只切斷了部落之間的共同療癒的機會,也反映出政府以漢人的世界觀來處置原住民族安置的需求。政府不只沒有去承認開墾、闢路、伐林等經濟行為對土地及生態的影響,安置時的永久屋措施也是以「幫助」為包裝的文化殖民。
漢人思維裡的房屋個人擁有權的觀念被強植在族人的生活空間,受助者只能被迫接受。莫拉克颱風後,約85%的原住民受災戶離開了村落,也離開了家鄉,但受災戶僅獲得房屋擁有權而非土地權,限縮土地使用、耕種、狩獵等,災民也應契約規定下而無法回到原鄉建構或是耕種,原住民族世界觀裡與土地萬物的連結不僅被漠視,且被以自認「助人」角度出發的被政府及民間團體切斷。[註二]。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也提到,災後支援需以關係為本,助人者應當尊重部落年齡階層組織及其決策的機制,助人者不應把自己擺置於「專業者」或「拯救者」的角度去指揮或對部落做出評斷,而是陪伴著族人及支持,從聆聽開始去了解、學習部落的規距、節奏、作息、社會架構、需求、知識、社區關係。[註三]
這一次,我們也希望政府在設計災後安置及復振計畫時能多跟在地社群對話,在助人的同時,能更加尊重族人的自決權,復原及重建的過程遠多於建構安置的房子,在中繼安置時,我們希望政府可以重視及支持部落的韌性,更多的聆聽、尊重、賦能。
註一:【花蓮救災浪漫化的微歧視】-- 原轉. Sbalay!
註二:永久屋:安居表象下的人權陷阱-- 台權會
註三: 馬太鞍溪溢流災後重建:社工進入Fata’an等部落指引--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
延伸閱讀:
救災時如何考量結構性不平等?重視部落傳統智慧-- 研之有物
人權立國的台灣,不應止步於災難邊界-- 林慧年老師
-
Ohay (阿美族,美國華盛頓州PAFATIS享想原流原住民族倡議聯盟理事長)
Nikal 杜芸璞(阿美族,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原住民族中心成員、法律博士候選人,美國華盛頓州PAFATIS享想原流原住民族倡議聯盟副理事長)
部落需要「中繼安置計畫」而不是永久屋
我們首先要呼籲:部落要的不是政府替族人決定,政府應聽見、尊重並實現部落的聲音,積極讓部落能在決策過程中,實質參與、有效溝通。
花蓮馬太鞍部落因堰塞湖溢流,洪水與泥沙吞沒族人的家園。災後的緊急清理與救援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受災居民接下來要如何安置?如何在重建過程中維持社群的力量與尊嚴?
近年來,政府常見的做法,是以旅館安置或推動永久屋建設,視為災後住宅政策的主軸。然這個政策常常沒有經過災民的同意或視災民的需要,而這次馬太鞍部落的聲音非常明確:部落要的是中繼安置計畫,不是永久屋。
為什麼是中繼安置計畫?
如黃舒楣老師所提醒,中繼安置不是隨便拼湊的貨櫃屋或工寮,而是一種為了「有尊嚴的生活」所設計的短期住居;必須同時兼顧家庭基本需求與社群共同空間,讓居民能夠安心住上一至三年,並在這段時間累積重建所需的資訊、討論與決策能量。
黃盈豪老師則進一步指出,中繼安置的核心意義在於「集體」:族人要住在一起,才能共同思索與面對家園的重建;把人拆散到各地的旅館房間,也許暫時舒適,卻削弱了社群的韌性與互助網絡,讓災民在孤立中面對艱難的生活復原。
部落的訴求:離災不離鄉
馬太鞍部落自救會已明確提出五大訴求,其中最核心的一點,就是「離災不離鄉」:拒絕永久屋,要求在傳統領域「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就地興建中繼住宅。
這樣的呼聲,並非僅是情感上的堅持,而是部落治理與文化脈絡的理性選擇。阿美族的年齡階層組織、教會體系、在地社群的互助模式,正是災後救援得以迅速展開的關鍵。若把族人分散安置,這些組織網絡將被切斷,重建動能也將被削弱。
我們想要一起呼籲:中繼安置不只是「暫時住的地方」,而是部落自我療癒、凝聚與規劃未來社群重建的必要基礎。
政府應立即行動
政府目前推動的「7+7旅宿安置方案」或以永久屋為導向的政策,無法回應馬太鞍部落的真實需求。若不及時調整,將重蹈九二一與莫拉克之後忽視社群、分散安置的覆轍。
因此,我們呼籲中央與地方政府:
立即盤點合適的土地,優先支持馬太鞍部落在傳統領域內設置中繼安置計畫;
在中繼安置的規劃過程中,保障族人充分參與決策,讓傳統部落組織與教會系統發揮力量;
在中繼安置的規劃裡納入公共空間、文化場域、生活產業等需求,而不僅是最小限度的「屋舍」。
此外,我們想特別強調:關於佛祖街受災嚴重的 89 戶由國土署協助評估宜居程度的租補、移居社會住宅等方案,目前政策走向並未釐清是否符合族人的想法與部落提出的中繼安置。我們想呼籲:政策應避免孤立化佛祖街的族人、迫使他們離開部落集體,並切勿在未與族人溝通的情況下,逕蓋集合住宅大樓,應理解原住民族文化,且更應讓居民站在能實質參與討論的主體位置,而不是被決定的客體;必須確保居民參與決策的時間、程度與範圍,族人的想法更必須被納入與尊重!
不要讓災難再度撕裂部落
災後重建不只是重建房屋,更是重建社會的關係網絡與文化的延續。若政策僅把災民視為「受補助的個別戶」,而不是「有自我治理能力的社群」,那麼重建將失去根基。
文末,我們想再引用黃舒楣老師的觀察,在日本東北、熊本、能登半島的災後重建中,中繼的設置提供的不僅僅是「屋頂」,還有公共設施、商店街、工坊,讓居民能延續生活感,保有社群的連帶,如此設計,才能讓人從災難的斷裂感中恢復,轉而孕育出新的未來。
馬太鞍部落的呼聲更提醒著:災後的安置必須以「部落」為單位,以「中繼安置」為核心。唯有如此,才能讓族人離災不離鄉,在尊嚴與自主中走向復原;這不僅是馬太鞍的需要,也是臺灣未來每一次面對災難時必須學會的課題。
參考資料:
Fata'an年祭 Facebook:部落五大訴求
黃舒楣,需要支持社群韌性的中繼安置規劃,臉書貼文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JGjf7ZiV8/
黃盈豪,馬太鞍下一步:為何災民要中繼安置?保留社區部落紋理成重建力量,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mataian-interim-housing-community
旅宿安置專案啟動 總統:中央全力支持花蓮,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509270103.aspx
Fata’an部落自救會憤怒 籲花縣府回應五大重建訴求,客新聞 https://hakkanews.tw/2025/10/01/232338/
呂玠鋆、陳泓屹、溫嘉楷 光復鄉89戶地勢低窪又受創 政府評估中繼宅、遷村,公視新聞網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773172
-
Nikal有很多名字,漢名和英文名,而族名是最晚走進他生命裡。當時他參與臺北市語言巢,同學的阿嬤幫未有族名的他取了這個名字,由老師拼音寫在一張小紙條上。當年族語書寫系統才開始被更多人熟悉,與現在比較常見的 Nikar拼音稍有不同(板上也有其他Nikar或Nikal嗎?來打招呼!)族語老師以大量歌謠帶學員認識字詞,對Nikal來說,一週一次、混齡的見面,除了是族語學習,更是一個難得機會能在臺北市接觸到其他阿美族的小孩。語言巢還有一項目標是要考族語考試,Nikal通過了許多測驗,但族語在嘴裡沒有鹽巴,長大後,一次在工作場合說了幾句族語,一前輩說:你的發音怎麼這麼可憐?
Nikal後來成為母親,正在美國讀法律。出國前逢疫情期間,開始接觸到一些全家能一起學族語的線上資源,到了美國後,持續從線上和臺灣帶來的族語繪本與小孩們一起學族語。小孩們在學齡前就到了美國,這些年來,家裡呈現多語言的狀態,但目前的困境是:小孩們的英文越來越好,中文維持可以溝通,而族語原地踏步。Nikal總在想:是不是自己還不夠努力?
當族語並非現在生活環境的主要溝通語言(這樣的敘述不只是像Nikal在海外生活的族人家庭會出現),族語使用是有賴特別維繫的,且更不是沒有困境的,但Nikal仍相信著:即便現在看似原地踏步、族語進度緩慢,只要每多一個單字、多一個詞、多一個聲音,加入了他與家人的腦海裡,那就是一顆種子。這個種子自帶養分且宜儲存,飽含阿美族的智慧和認識世界的方式,並會在某一天,當溫度和溼度都適當了,就開始發芽。
-
慧喻透過他的博士論文研究,與鄒族山美部落教室老師、學生家長、以及社區族人深入對話,認識並紀錄部落教室的母語與文化傳承工作。 鄒族山美部落教室在2002年成立,最初只是為了協助社區農忙的家長,讓孩子們放學後有一個安全的空間,由一群部落媽媽陪伴與與學習。隨著時間的推移,部落教室漸漸發展成母語與文化學習保存的重要場所。今天,部落教室走過二十幾個年頭,從課後輔導到母語文化的保存,再再展現了山美社區與族人的韌性與堅持。
透過課堂觀察與老師們的深度訪談,慧喻記錄了部落教室的教學與學習活動是如何地呈現鄒族的世界觀與傳統價值,這種連結在文化與母語保存工作上至關重要。然而,就像Nikal的經歷一樣,山美社區族人也面臨了因為族語並非主流語言,而必須付出更多心力去維繫與保存的挑戰。儘管長期面對主流文化敘事的挑戰,山美部落教室仍不懈地實踐鄒族文化與母語的教學,確保下一代能夠維持並傳承鄒族的文化。透過部落教室的工作,老師們也期盼能種下一顆顆熱愛自身文化、擁抱與認同自己的種子,最後開花結果,將文化傳承工作視為自己的使命與責任。對這些部落教室的孩子而言,部落教室就像家,帶著你認識自己、認識文化。而這個家,永遠都在。
文末,我們也向大家分享幾個目前PAFATIS有認識的族語復振的團體與他們的社群連結(更歡迎大家在留言補充你們知道的團體或資源!)
Pipalofasaran to Sowal no Pangcah/'Amis 台灣阿美族語言永續發展學會/原民會阿美族語言推動組織
-
身為天天都在吃滷肉飯的臺灣在地人,當滷肉飯被當作展演臺灣小吃文化的元素,然而其中的滷肉卻被其它類似的食材取代。你認為這樣所謂代表「臺灣小吃」的活動能夠真正展現臺灣在地的小吃文化嗎?
去年加拿大《Dragons’ Den》(註一)的節目裡面有一組創業團隊推出名叫Bobba的瓶裝珍珠水果茶,宣稱比原本「很流行但成分不明的含糖飲料」更健康。這個產品雖明顯打著珍珠奶茶的名號標榜更健康,但推銷的過程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臺灣就是珍珠奶茶的文化出處。雖然被演員 Simu Liu 當場質疑後表明團隊有跟臺灣的廠商合作,但整個過程被質疑並沒有尊重珍珠奶茶的文化淵源。
類似的經驗很多臺灣原住民族族人應該也有過。2022年夏季由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aiwan in San Francisco)在所舉辦的僑務活動中安排了一場「活力小排灣」的表演中,幾位表演者的服飾明顯不是臺灣排灣族的傳統服飾。這些照片在族人們質疑後,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才下架在臉書上有疑慮的活動照片 (註二)。
遺憾的是,今年八月,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參訪馬紹爾群島、夏威夷及關島時穿著符號化後的原住民族的服飾,表演主流漢人文化下所認為的「原民舞蹈」,藉以宣揚臺灣的多元文化。
我們理解因為原住民族各族文化有別於在臺灣主流的漢人傳統文化,政府出自於讓受眾體驗臺灣多元文化的美意。然而因為有別於主流的生活文化,政府很容易因為不熟悉、沒有通盤了解,也沒有讓原住民族族群主導自身的文化展演設計而造成曲解與誤用。在台灣的原住民族服飾、傳統、舞蹈、音樂以及其他文化在國際上被用為台灣的文化推廣的同時,這個過程中,是否忽略了原住民族對自身文化定義的權利?是否忽略了,在台灣長期殖民結構下,原住民在保留其文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結構性壓迫?
上述這些事件中凸顯了社會中族群權力不對等的關係。在公共宣傳及文化展演的活動中,主流文化掌握了資源、話語權與呈現方式,非主流族群的文化常常被簡化與符號化,甚至失去了自己詮釋自己生活文化的權力。即使政府是出自於良好初衷在規劃這些活動,如果忽略了文化持有者的聲音及歷史脈絡,這些文化的展示就會成為錯置,更加重現了結構性的權力不平等問題。
我們期待未來政府在推廣多元文化時能夠尊重族群自主權,將非主流族群朋友們視為平等的夥伴共同參與活動設計。唯有如此,多元族群文化才能以自己的方式呈現與讓社會瞭解。
註一:新聞來源為 Bubble tea company apologizes after Dragons' Den cultural appropriation spat | CBC News
註二:還有更多例子可以參考《當原民服裝成為校園演出的道具?你眼裡的「文化展示」,是對我傷口的踩踏》人文思想
https://plainlaw.me/posts/When-Indigenous-clothing-becomes-campus-performances
「土地不是我們從祖先繼承而來,而是向後代子孫借的。」